
研究者都认为魏晋六朝的小说祇能算成古代小说的构成期,而唐代传奇则开展到成 熟阶段。那么二者的区别安在?鲁迅先生曾有如下阐述:
单从上述那些素材来看,武断的说起来,则六朝人小说,是没有记叙仙人或鬼魅 的,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;文笔是简洁的;素材是笑柄,谈资;但似乎很排
斥虚构……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:
仙人人鬼妖物,都能够随意差遣;文笔是精巧,盘曲的,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;所叙的事,也大致具有首尾和波涛,不行一点断片的谈柄;并且做者
往往有意展现着那事迹的虚构,以见他想象的才气了。[1]
此中,文笔的「简洁」与「精巧」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之一。
无论读者仍是研究者,都把细节描写做为成熟小说的一项重要原则。
小说不是以抒 爆发者小我豪情为目标,而是以实在再现社会生活为目标,所以,生活的细节愈多才愈实在。
应该认可,与西方小说比拟,模仿平话艺术叙事办法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,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上,稍逊一筹。但跟着小说艺术的开展,细节与心理的
感化逐步被做家熟悉。到了《金瓶梅》,白话小说的细节描写已经有了长足的朝上进步。
那里我们比照一下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对武松杀嫂那一情节的差别处置体例:
那妇人见头势欠好,却待要喊,被武松脑揪倒来,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,扯开 胸膛衣裳,说时迟,那时快,把尖刀往胸前祇一剜,口里衔着刀,双手却斡
开胸膛脯,取出心肝五脏,供养在灵前。肐查一刀,便割下那妇人头来,血流满地。[2]
不异的情节,《金瓶梅》的描写就有差别:
那妇人见头势欠好,才待大喊,被武松向炉内挝了一把香灰,塞在他口,就喊不 出来了,然后脑揪番在地,那妇人挣扎,把鬏髻簪环都滚落了。
展开全文
武松恐怕他挣扎,先用油靴祇顾踢他肋肢,后用两只脚踏他两只胳膊,便道:「淫妇,自说你伶俐,不晓得你心怎么生着,我试看一看!」一面用手往摊
开他胸脯,说时迟,那时快,把刀子往妇女白馥馥心窝内祇一剜,剜了个血窟礲,那鲜血就邈出来。那妇人就星眸半闪,两只脚祇顾登踏。
武松口噙着刀子,双手往斡开他胸脯,扑扢的一声,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,沥沥供养在灵前。前方一刀,割下头来。血流满地。[3]
《水浒传》89 字,《金瓶梅》则扩大为213 字,把武松手刃潘金莲的过程写得更为 详尽。
其差别次要表示在武松的动做增加了(塞香灰、踢肋肢、骂)。《水浒传》祇把视点落在武松身上,《金瓶梅》则在二者之间游动,也写出了潘金莲被杀
时的挣扎苦相(鬏髻簪环滚落、鲜血冒出、星眸半闪、两脚登踏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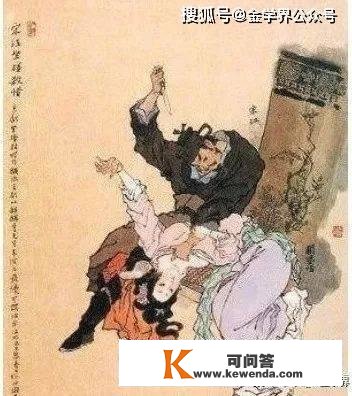
绘画 · 武松杀嫂
《金瓶梅》和《水浒传》的着重点是差别的,《水浒》重在写武松,《金瓶梅》则是将潘金莲做为叙事的焦点人物。
在笑笑生的笔下,潘金莲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,都是细加描绘的;那么当她的生命行将完毕时,做者当然更不肯吝惜翰墨。
试想标致而凶恶的潘金莲,她的鬏髻簪环,她的皓齿明眸和「白馥馥」的胸膛曾引得几狂蜂乱舞。但现在却是「簪环滚落」,「星眸半闪」,白馥馥的
心窝上「剜了一个窟礲」!那是多么强烈而又可怕的比照!
做者把那个血淋淋的杀人排场展现给读者,细细地玩味着潘金莲的痛苦,显然包罗着对那个险恶女人的仇恨,似乎祇有用那种惨绝人寰的结局体例方可使
她赎回本身一生的罪恶。
武松在那里再也不是梁山泊的起义英雄,做者祇把写成一个通俗的杀人刽子手。杀嫂排场的详尽描绘,将其性格中残暴的一面推向极致。
超卓的细节描写,在《金瓶梅》中俯拾皆是,对表示人物的特殊性格起到画龙点睛 的艺术效果。
张竹坡对兰陵笑笑生的那一胜利的艺术手法赐与很高评判:「文笔无微不出,所认为小说之第一也。」[4]「千古稗官家不克不及及之者,老是此等闲笔难学
也。」[5]
所谓「闲笔」者,恰是在一些具有特殊感化的细节描写。
再第五十九回写官哥儿身后,李瓶儿伤痛欲绝:
「李瓶儿见不放他往,见棺材起身,送出到大门首,赶着棺材大放声,一口一声祇喊:『不来家亏心的儿嚛!』喊的连声气破了。」[6]
做者似仍嫌不敷,接写李瓶儿「到了房中,见炕上空落落的,祇有他耍的那寿星博浪鼓儿还挂在床头,一面想将起来,拍了桌子,由不的又哭了。」[7]寿
星博浪鼓儿,是官哥满月时薛寺人送的喜礼。
此时官哥儿已死,做者却偏偏从那个博浪鼓儿进手,写出李瓶儿睹物伤情的无限哀思,可谓奇绝笔法!所以张竹坡在此批道:「小小物事,用进文字,便
令无限血泪,皆向其中洒出。实是奇绝文字。」[8]
像那类看似「闲笔」的细节,其实涵蕴著做者的艺术匠心,在故事中起着不成替代 的感化。再如做者写潘金莲有一个习惯动做:跐着工具磕瓜子儿。每一次
呈现那个动做,都包罗着差别的含义,反映着仆人公的差别心境。
第十五回,潘金莲嫁给西门庆后,与孟玉楼等登楼看灯:
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,显他那各处金掏袖儿,露出那十指春葱来,还 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,探着半截身子,口中磕着瓜子儿,把磕了的瓜子皮都
吐下来,落在人身上,和玉楼两个嘻笑不行。[9]
一副轻佻、卖弄的心理!新婚燕尔,身进温存富贵之乡,她又怎能压制住心里的自得和 称心?
在那个「看灯的人挨肩擦背,仰看上瞧」的罕见场所,不赶急炫示夸耀本身的虚荣,还要更待何时呢?但当她的强硬敌手李瓶儿就要为西门庆生下贵子的
时候,潘金莲固然外表上「用手扶站庭柱儿,一只脚跐着门坎儿,口里磕着瓜子儿,」
似乎显得悠闲自得,毫不在意,但当听到孩子生下来时,末于掩饰不住心里的忌恨和仇恨,跑进房内关起门失声痛哭起来。
此时「跐着门坎儿磕瓜子」的细节,现实上正表示了她的虚弱不胜的心理。

戴敦邦绘 · 李瓶儿
李瓶儿母子相继身后,潘金莲成为成功者,实现了她专宠的目标,那时,她又从头恢复了昔日的自得:
那玳安引他进进花园金莲房门首,掀开帘子,王婆进往。见妇人家常戴着卧兔儿, 穿戴一身锦缎衣裳,搽抹的如粉妆玉琢,正在房中炕上,脚登着炉台儿,
坐的嗑瓜子儿。房中帐悬锦绣,床设缕金,玩器争辉,箱奁耀日。[10]
关于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,有「跐门坎」「登炉台」之类的动做,是不雅观的行为,祇有 悍妇和凶恶的女人才会有。
《红楼梦》中的王熙凤也常有那个动做。如:
宝玉食了茶,便出来,不断往西院来。碰巧走到凤姐儿院门前,祇见凤姐蹬着门 槛子拿耳挖子剔牙,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。[11]
根据老北京的端方,大姑娘小媳妇绝对不准跐门坎儿,因为跐门坎儿不是良家妇女 所为。
曹雪芹对北京风俗当然很清晰,但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动做安到王熙凤身上呢?我们祇能认为,那绝不是曹雪芹的忽略,而是有意为之。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借僧人之口,主张小说要记述「家庭闺阁中的一饮一食」,要描写那些「琐碎细腻」的生活细节,反对小说「祇传其可能」。
曹雪芹显然重视到《金瓶梅》中的「跐门坎」「嗑瓜子」如许的细节,对描绘潘金莲的特殊性格有重要感化,那才移用到王熙凤身上,塑造出另一个心狠
手毒的「冷美人」形象。那也是他对本身的写「琐碎细腻」生活主张的理论。
细节描写既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标记之一,也是模仿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门。
细 节描写的大量增加和敏捷成熟,其实不单纯是小说身手问题,它反映了古代小说看念的一个改变,即中国传统的侧重「叙事」的小说正在向「模仿」体小说
转化。
那是古代平话体小说向现代小说体小说开展的一个重要步调。模仿是西方美学思惟的一大收柱,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「文学起源于模仿」说。
亚里士多德说:
「起首模仿是人的一种天然倾向,从小孩时就显出。……人一起头进修,就通过模仿。每人都天然地从模仿出来的工具得到快感。」
他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是客看存在的模仿物:「人们看到逼肖原物的形象而感应欣喜。」[12]而要到达模仿的传神、生动,细节的实在描写就是
必不成少的。
因而,在那种意义上说,细节描写的胜利就意味着整个小说艺术的胜利。
《金瓶梅》既没有令人崇敬、敬畏的英雄人物,又没有惹人进胜的传奇故事,祇是写了一群道德沦丧的男女,一些普通的家庭生活,为什么能产生浩荡的
艺术力量呢?
部门原因正在于它以一个又一个令人心服的细节描写「再现」了生活的「原物」,人们从那些艺术化了的「原物」上获得了「快感」,即艺术的美感。
以模仿宋元说话艺术而构成的白话小说,是典型的「论述」体文学。做者历来不隐 瞒本身的实在成分,不竭以「看官传闻」的形式介进做品,停止公开的理
性说教或对人物、情节停止阐释、评论、阐明,故事中的一切都是颠末做者之口转述,而非主动的展示。
《三国》《水浒》表现了那种论述体小说的根本特征。《金瓶梅》固然并未完全脱节平话体小说的形式,但其运用戏剧化手法模仿生活的成份大大增加。
读者对做品中的虚构世界更多的是通过做品人物的「自我表示」间接看察,而不需由做者的转述间接领略。显然,模仿比论述更具生活的实在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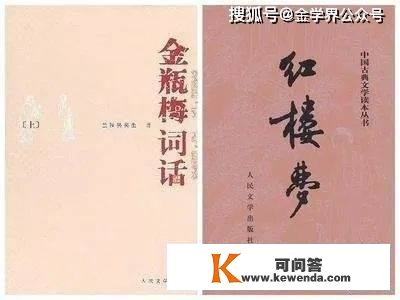
《金瓶梅》与《红楼梦》
张竹坡曾指出《金瓶梅》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法:
《金瓶》有节节露马脚处。如窗内淫声,僧人偏闻声;私琴童,雪娥偏晓得;而裙 带葫芦,更属险事;墙头密约,金莲偏看见;蕙莲偷期,金莲便碰
着;……烧阴户,胡秀偏就看见。诸如斯类,又不计其数。……此所认为化笔也。[13]
现实上,张竹坡指出了《金瓶梅》的一个重要叙事技法,那就是操纵人物的感官做为一 个特殊角度,既做为生活细节的展现办法,又为情节的停顿埋下伏
笔。
张竹坡说的「窗内淫声」是指第八回「潘金莲长夜盼西门庆,烧夫灵僧人听淫声」中的情节:
本来妇人卧房,正在佛堂一处,行隔一道板壁;有一个僧人先到,走在妇人窗下 水盆里洗手,突然闻声妇人在房里,颤声柔气,呻嗟叹吟,哼哼唧唧,好似
有人在房里交姤一般。
于是推洗手,立住了脚,听勾好久。祇听妇生齿里嗽声唤喊西门庆:「达达,你休祇顾打到几时,祇怕僧人来闻声,饶了奴,快些丢了罢!」
西门庆道:「你且休慌!我还要在盖子上烧一下儿哩!」不想都被那秃厮听了个 不亦乐乎。[14]
正在为武大烧灵超度的时候,西门庆又与潘金莲行淫,当然是在极私密的形态下进 行的。
做者认为假设像「醒闹葡萄架」那样正面描写,显然与超度排场反差太大,有违情理。于是祇从听觉的角度,表示二人「颤声柔气,呻嗟叹吟,哼哼唧
唧」的声音,并让僧人听到,并且因而宣扬开来,以致寡僧都「不觉都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」起来。
那种手法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,既表示了西门庆、潘金莲的淫荡无行,又表示了僧人的「鬼乐官」和「色中饿鬼」的素质。
类似的写法书中良多,潘金莲之所以被做者付与「专一听篱察壁」的习惯,在很大意义能够说,是做者付与了她更多的叙事功用,以她的听觉来表示情
节。
如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李瓶儿在翡翠轩内行事,潘金莲便「回来静静蹑足,走到翡翠轩槅子外潜听」,成果「闻声西门庆向李瓶儿道:『我的心肝,你达
不爱此外, 爱你好个白□□儿。』……李瓶儿道:『不瞒你说,奴身中已怀临月孕。』」潘金莲那 一听,不单第一时间得知李瓶儿怀孕,立即对西门庆和李瓶
儿冷言冷语,并且深恐瓶儿威胁她的专宠地位,从此立下了害李之心。
张竹坡认为那种写法是以险笔写「情面之可畏」,天然有事理;但从做者叙事的角度而言,除表示了潘金莲的阴险性格,也是鞭策情节开展的手法。
把叙事使命交给做品人物,巧妙操纵各类感官功用做为特殊的叙事看点,也是做者 的一种模仿身手,比做者亲身论述更显得客看实在。
平话体的中国白话古代小说,那种写法良多。天然光景,社会排场,人物的容貌服饰,都能够用「祇见」「但见」之类的套语,通过人物的眼睛来展现。
如话本小说中就有良多如许的写法:
相如举目看那园中景致,但见:径展玛瑙,栏刻香檀。聚山坞光景,为园林景物。
山迭岷岷怪石,槛栽西洛名花。梅开庾岭冰姿,竹染湘江愁泪。春风荡漾,上林李白桃红;秋天凄凉,夹道橙黄桔绿。池沼内鱼跃锦鳞,花木上禽飞翡
翠。[15]
祇见一个着白的妇人出来驱逐,小员外着眼看那人,生得:绿云堆鬓,白雪凝肤。
眼描秋月之明,眉拂青山之黛。桃萼淡妆红脸,樱珠轻点绛唇。步鞋衬小小金莲, 十指露尖尖春笋。若非洛浦仙人女,必是蓬莱阆苑人。[16]
操纵人物 的眼睛做为一个特殊的叙事角度,那是古代白话小说做者早已娴熟运用的技 法。

万历本
话本小说及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中都能够找到大量例证,兰陵笑笑生也深得个中三昧。
如潘金莲初进西门庆大官人之家,她和吴月娘诸人彼此对看,就写得很超卓。
《金瓶梅》 第九回有如下一段描写:
月娘在坐上,认真定睛看看:那妇人年纪不上二十五六,生的如许美丽,但见: 眉似初春柳叶,常含着雨恨云愁。……看了一回,口中不言,心内暗道:
「小厮每家来,祇说武大如何一个妻子,未曾看见。今日公然生的美丽,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。」
那边潘金莲也在看吴月娘:
那妇人坐在旁边,不转睛把眼儿祇看吴月娘,约三九年纪,因是八月十五生的, 故小字喊做月娘。生的面若银盆,眼如杏子。……那妇人一抹儿多看到心
里。[17]
那一场景是潘金莲嫁到西门庆家后的第一幕。
一边是「认真定睛看看」,另一边是 「不转睛」地看,构成一幅饶有兴味的画面。 两边的边幅都由对方的视觉中映出。
吴月娘 何以要「认真定睛看看」? 仅仅是为证明小厮们对金莲长相的赞扬吗? 非也。
固然做者 把吴月娘写得宽浩荡度,但那个「认真定睛看看」,正阐明她在专心探究「俺那强人」 为什么要爱她; 最少要在金莲的容貌上证明一下是
否值得「俺那强人」的爱。
成果认可 金莲确实「生的美丽」,弄清了西门庆爱她的原因。 关于刚到目生情况的潘金莲来说, 最迫切的是对那个新情况的领会; 而最间接的办法,
莫过于亲眼看看。
做者将吴月娘和 李娇儿等寡妇人的长相放在潘金莲的眼中看出,是足够体味她亦急于见到那些人的心 情。 固然两边都急于见到对方,领会对方,但目
的却不尽不异。
月娘莫非仅仅是为了探 讨西门庆爱潘金莲的原因吗?当然不是。我们从她的口气里能够发现,她是遭到一股妒 火的差遣。
而金莲则是在谋求计谋,她本能地觉得到,几个强劲的敌手早已在那里等着 她,她必需尽快地找出计谋来,不然便难有安身之地。
像潘金莲如许有心计的女人,她 很清晰本身面临的那几个女人,不只是本身的伙伴,更是敌手。
张竹坡又云: 「内将月 娘世人俱在金莲眼中描出,而金莲又重在月娘眼中描出。 文字生色之妙,全在两边掩 映。 」[ 18]
对读者来说,等于操纵两边的眼睛看到对方的边幅,易产生设身处地之感,比 由做者口中叙出更具艺术效果。
对景物和排场的描写,《金瓶梅》也多用人物视觉看点,并多有「祇见」「但见」 做前导词。
如「吴月娘在家整置了酒肴细果,后同李娇儿、孟玉楼、孙雪娥、大姐、潘 金莲,世人开了新花园门, …… 但见: 正面丈五高,心红漆绰屑; 周
围二十板,砧炭乳 口泥墙 …… 」
「但见: 万里浓云密布,空中祥瑞飘帘,琼花片片舞前檐 …… 」有时还可 以操纵人物视觉看点的不竭变更,映出连续串的动做行为,使情节内部的各
种因素密切 地连络在一路。 如第七十九回:
到次日起来,头沉,懒待往衙门中往,梳头净面,穿上衣服,走到前边房中,笼 上火,那里坐的。
祇见玉箫早晨来如意儿房中,挤了半瓯子奶,径到配房,与西门庆食药,见西门庆倚靠在床上,有王经替他打腿。
王经见玉箫来,就出往了。打发他食药,西门庆喊使他拿了一对金裹头簪儿,四个乌银戒指儿,教他送来爵媳妇子屋里往。
那一段写得很细,能够说全由不起眼的细节构成。假设把那连续串动做朋分一下, 则是:
①论述人见西门庆在书房里坐的。
②西门庆见玉箫儿如意儿房中挤奶。
③玉箫儿 见王经替西门庆打腿。
④王经见玉箫儿打发西门庆食药。 ⑤论述人见西门庆使玉箫送东 西。
①是论述人的视角,②③④的排场都放在做品人物的视觉中写出,到了⑤又回到叙 述人的视点上来。
从人物视觉的角度反映描写对象,那种写法的长处在于更随便形成模仿的「幻觉」, 更接近生活自己的实在。
就生活的现实情形来说,任何工作的发作都必需亲眼看到或亲 耳听到,人们才易于认可那件事确曾发作过,也便是说,必需有见证人。
而小说中的事 件,多是由论述人(做者)反映的,读者认可论述的实在要有一个前提,即论述人必需是 诚恳的。
论述人当然是一位「全知的神」,但比力而言,人们甘愿相信做品中戏剧化了 的人物,更相信一心一意的眼睛或听觉。
由做品人物眼睛所看出的工具,不只具有客看实在性,同时也不成制止地蒙上人物 的主看色彩,有时那种主看色彩比客看性更重要。

《金瓶梅》连环画 · 西门庆之死
在我们所举的吴月娘和潘金莲对看的 例子里,两人眼中看到的一切,现实上已染上一些她们小我的感情。
再如第二回潘金莲 和西门庆初度相见:
妇人便慌忙陪笑,把眼看那人,也有二十五六年纪,生的非常博浪:头上戴着缨 子帽儿,金小巧簪儿,金井玉栏杆圈儿,长腰身穿绿罗褶儿,脚下细结底陈
桥鞋儿,清水布袜儿,腿上勒着扇玄色桃丝护膝儿,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,越显出张生般庞儿,潘安的貌儿,可意的人儿,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与奴个眼色儿。
西门庆眼中的潘金莲则是:
黑鬓鬓赛鸦翎的鬓儿,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,清泠泠杏子眼儿,香馥馥樱桃口儿, 曲隆隆琼瑶鼻儿,粉浓浓红艳艳腮儿……[19]
做者巧妙运用了儿化韵的修辞手法,详尽地描写二人的穿着、长相,共享了二十六 个「儿」字。
勿庸置疑,那种细密的描绘有介绍出场人物外表的感化,但更次要的,特 别是连续串儿化韵的运用,与其说是描画二人的描摹,不如说是二人彼此挑
逗、吸引的 豪情流露,恰是那富有弹性的觉得中,显露出他们轻佻、飘荡的性格。
操纵做品人物的言语叙事,也是一种模仿的体例;亦即柏拉图所云「诗人尽量形成 不是他本人在说话」,而是由他人在讲话,担任叙事使命的假象。
言语做为一种传达信 息的东西,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扬重要感化,在小说中,祇把言语做为一种叙事看 点,即做家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角度,而不
仅仅充任故事人物之间的寒暄东西,它才显 得更有意义。
张竹坡对《金瓶梅》的言语看点叙事甚为赞扬,在第三十五回批道: 「此 回单为书童超卓描写也,故上半篇用金莲怒骂中衬出,下半篇用伯爵笑话中点
醒也。 」
书童是个供人玩乐的男宠,与西门庆有暗昧关系,对那个特殊人物,做者不正面描写, 而放在「金莲怒骂」和「伯爵笑话」中叙出,确是奇绝笔法。
张竹坡还对崇祯本《金瓶 梅》将武松打虎情节放在应伯爵口中说出大为赞扬:
《水浒》上打虎,是写武松若何踢打,虎若何剪扑,《金瓶梅》却用伯爵口中几个 怎的怎的,一个就像是,一个又像,以致《水浒》中费多么力量方写出
来者,他却一毫不吃力便了也,是多么灵滑手腕。[20]
差别叙事角度的运用,与做者要到达的艺术目标密切相联。《水浒》写的是武松, 对能表示其豪勇性格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,所以摘取做者旁看的写
法,对武松的一 招一式,一拳一脚,虎的一扑一掀,一剪一吼都细加描绘,增加细节的实在感,以形成 触目惊心的气氛。
《金瓶梅》是以西门庆、潘金莲等做为次要描写对象,将武松放在应 伯爵口中叙出,就使情节变得愈加精炼、集中。

戴敦邦绘 · 潘金莲
从那一点来说,崇祯本《金瓶梅》确实 比词话本更懂得人物言语看点的妙用。 操纵人物转述故事内容,有时是情节的需要,不能不如斯。
如第六十四回李瓶儿死 后,傅伴计与玳安有一段对话。 当傅伴计闲话中说起西门庆发送李瓶儿之事,玳安说道:
一来是他福好,祇是不长命。俺爹饶使了那些钱,还使不着俺爹的哩。俺六娘嫁 俺爹,瞒不外你白叟家晓得,该带了几带头来?他人不晓得,我晓得。把
银子休说,祇光金珠玩好、玉带绦环鬏髻、值钱宝石,还不知有几。为甚俺爹心里疼?不是疼人,是疼钱!
玳安是西门庆的心腹小厮,对奴才侵吞花家财富之事知之甚详,并且必定还晓得更 为隐秘的事,由他来道西门庆心中的奥秘,显示他与李瓶儿关系的另一个
侧面─金钱 与恋爱,显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。
做者无意使读者对西门庆的性格本色与李氏关系产生 曲解,所以将玳安的话偏偏放在西门庆对李氏葬礼若何不吝财帛,对李氏若何伤悼的种 种虚假表
演之后; 假象与本色的强烈比照,也产生了明显的挖苦效果。
还有一种情状是以做品人物的言语表示本身,有时还配以动做;比力而言,那种写 法的戏剧化味道更浓一些。
如李瓶儿要生孩子,潘金莲妒火中烧,非常愤怒,就有一段 相当超卓的戏剧化演出。 她对孟玉楼说孩子不是西门庆的骨血:
「我和你恁算,他从往年八月来,又不是黄花女儿,昔时怀进门养?一个后婚妻子, 汉子不知见过子几,也一两个月才生胎,就认做是咱家孩子!我说
差了,若是八月里生孩子,还有咱家些影儿;若是六月的,小板橙凳糊险道神─还差着一帽头哩。失迷了家乡,那里觅犊儿往?」
正说着,祇见小玉抱着厕纸、绷接并小褥儿来。
孟玉楼道:「此是大姐姐预备下他迟早临月用的对象儿,今日且借来应急儿。」
金莲道:「一个大妻子,一个小妻子,明日两个对养,非常养不出来,细碎出来也罢。俺们是买了母鸡不下蛋,莫不杀了我不成?」 又道:「仰着合
着,没有狗咬尿胞虚欢喜。」
玉楼道:「五姐是什么话!」以后见他说话出来,有些不防思维,祇垂头弄裙子,其实不出声应答他。潘金莲用手扶着庭柱儿,一只脚跐着门坎,口里磕
着瓜子儿。
祇见孙雪娥闻声李瓶儿前边养孩子,后边从容不迫,一步一跌走来看看,不防黑影里被台基险些未曾绊了一交,金莲看见,教玉楼:「你看献勤的小妇
奴才,你渐渐走,慌怎的?夺命哩?黑影子绊倒了,磕了牙也是钱!姐姐,卖罗卜的拉盐担子,攘咸嘈心,养下孩子来,明日赏你那小妇一个纱帽戴?」
好久,祇听房里呱的一声,养下来了。……那潘金莲闻声生下孩子来了,百口欢喜,乱成一块,越发怒气生,走往了房里,自闭门户,向床上哭往了。
[21]
那一段写得极细,几乎全由人物言语和动做构成,「镜头」的转换相当快,表示了 潘金莲、孟玉楼、孙雪娥等几小我对李瓶儿生孩子的微妙立场,非常形象
生动。
特殊是 对潘金莲在一霎时的心理改变,很有条理地展示给读者。 一起头,她在李瓶儿怀孩子的 时间上做文章,以证明各人不应自觉为那个「失迷了
家乡」的「犊儿」兴奋; 继而又骂 西门大姐是西门庆的小妻子,并狠毒地咒骂「非常养不出来,细碎出来也罢」; 再下来 骂孙雪娥; 最初,孩子下地
了,潘金莲却在一片喜洋洋的气氛中,「向床上哭往了」。
那连续串的镜头,完全而清晰地映照出潘金莲那个险恶女人由忌恨到愤怒,由愤怒到诅 咒,由咒骂到失看而痛哭的阴暗心理的整个活动过程。
那里还夹着两处动做描写,是做 者看察视点。 一个是写潘金莲气急松弛地骂东骂西时「用手扶着庭柱,一只脚跐着门坎, 口里磕着瓜子儿」,像一幅
人物特写镜头,照出一个色厉内荏的悍妇形象。
此时的潘金 莲虽又气又恼,却有意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,想用外表的平静掩饰心中的不安和妒 火; 二是写金莲「越发怒气生,走往了房里,自闭
门户,向床上哭往了」,反映了她在 事实面前末于失看,表露出一个「失败者」无法的心理形态。

《漫话》孟昭连 著
注 释:(从略)
文章做者单元:南开大学
本文获受权颁发,原文刊于《孟昭连金瓶梅研究精选集》,2015,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书。转发请说明。
